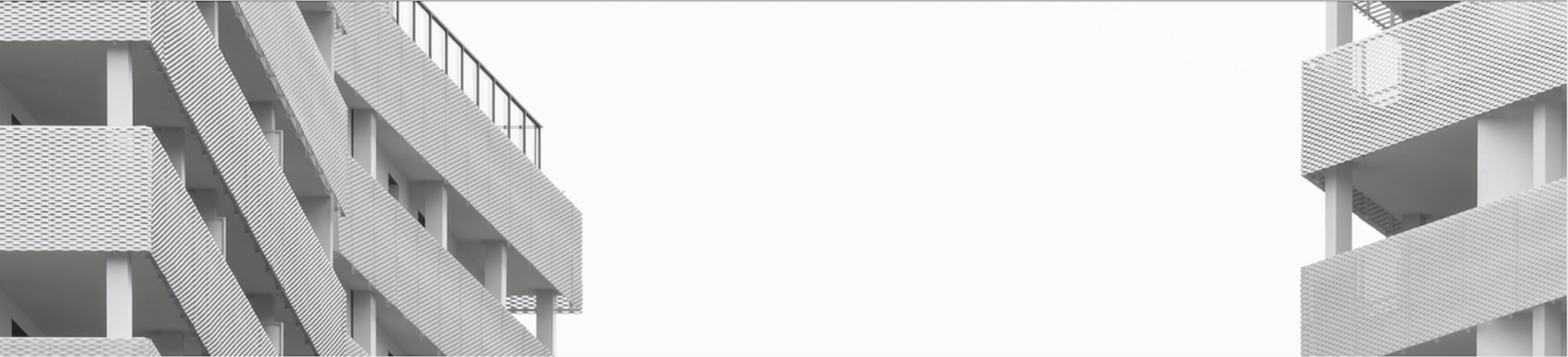声驰首页 > 声驰动态 > 声驰资讯 > 内容标题
执行异议若干实务要点解析
一、问题的提出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司法执行实务的难题,但这一难题在近些年得到了有效改观。一方面,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大修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的有关执行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达34件。通过这些文件的出台,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有关执行措施、执行分配制度、执行救济程序等内容,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最高院在2016年全国“两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而后法院执行工作一直处于“高压”状态,2018年更是被称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年。基于此,“执行难”得到基本解决是可期的。但与之相比,有关执行救济程序的规范仍有待完善,特别是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标的异议如何区分以及实务中仍大量存在的“已裁代审”“以裁代行”等情形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造成实务中认知、裁判的混乱。笔者认为,针对此类问题有必要加以厘清。
二、执行异议的分类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225、第227条依据执行异议对象的不同,将执行异议分为执行行为异议、执行标的异议,并针对两种异议设计了不同的处置方式、法律效果。但前述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据此最高院制定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为执行异议的实务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可即便如此,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亦未对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标的异议的区分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异议人、执行法院在提出执行异议、审查异议案件时的法条援引出现混乱,特别是当事人以外的人提出异议时,如何判断其究竟是执行行为异议中的利害关系人,还是执行标的异议的案外人成为难点。笔者认为,前述两种异议的有效甄别,应当采取形式判断与实体判断相结合的方法,即首先根据异议主体加以判断,再行考察异议所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具体判断路径为:(一)异议主体。
根据民诉法第225、第227条规定,执行行为异议的主体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执行标的异议的主体为案外人。其中,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均为执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故执行异议主体为当事人的,则其只能依据民诉法第225条提起执行执行异议,此时仅做形式判断即可,无须实质分析异议对象究竟是执行行为或执行标的。当然,此种判断亦仅限于异议主体为当事人的情形,若异议主体为当事人以外的人的,则须按照第二项标准加以区分。
(二)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
从上述两种异议制度创设的目的来看,执行行为异议的目的在于纠正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以维护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程序上的利益;而执行标的异议的目的在于排除对特定标的执行,以保护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利。故二者的区分,特别是“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的区分,应紧扣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如果异议对象是执行标的物,且依据的是对该标的物享有的所有权等足以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则构成执行标的异议。反之,如果异议对象仅限于执行行为,或异议对象为执行标的物,异议人对该标的物亦享有实体权利,但该实体权利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比如排除超标的查封、法院违法拍卖侵害异议人对标的物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的,则为执行行为异议。即执行标的异议实体上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异议人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二是该权利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需注意的是,这里的的权利不仅仅局限于所有权,还包括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可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规定,异议人系待执行不动产的买受人,其在该不动产被查封前已签订有效书面合同且合法占有、支付价款的,可依据享有的债权申请排除强制执行该不动产。
简言之,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标的异议应按照异议主体之形式判断与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之实体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加以区分。前述两种异议中的“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虽同属执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但其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大不相同。因此,只有充分理解两种异议的实质性内涵,方能在实务中准确援引、适用相对应的法律条文。
三、执行异议若干争议情形
随着近些年执行措施的增多、执行力度的加大,相应执行异议案件的数量亦随之增加,其中一些异议情形因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成为实务难点。笔者以在实务中常见的且具有较大争议的三种异议情形为例,以探讨相应执行行为之合法性。
(一)执行中能否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
实务中,不少法院在被执行人无财产或无足够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裁定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笔者认为,该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且有违民诉法基本原理,属“以执代审”,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
1、违反民诉法基本原理
执行仅为实现生效判决内容,其不能突破或改变生效判决确认的责任承担主体等实体内容,涉及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及责任承担主体等实体问题只能在审判阶段解决。在执行中以裁定方式确认执行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被执行人配偶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等实体内容,并继而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追加异议人为被执行人,显属“以执代审”,明显突破了生效判决对案涉债务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
2、无法律依据
最高院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的变更、追加专门制定了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详细列举了民事执行中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且无兜底条款。其列举的情形中并不包括追加判决确认的债务人配偶为被执行人。另从该解释的精神看,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仅限于原被执行人死亡、注销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而仅因被执行人缺乏清偿能力,就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亦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精神。
3、最高院早已严禁此类追加
最高院数次通过判例、新闻发布会等方式阐明“执行不能改变判决”“严禁以执代审”。特别是2016年3月3日,最高院杜万华法官答记者问时,明确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本身就是司法审判的裁判标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只能在审判阶段不能在执行阶段。”,并特别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认定。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
(二)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审批,能否裁定对商业银行股份“以物抵债”或拍卖后归购买者所有
实务中,不乏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为商业银行股份的情形。一些法院在对该股份处置时,通常先行拍卖,拍卖成功的,裁定该股份归购买者所有;两次流拍的,裁定“以物抵债”,即该股份归申请执行人所有。上述做法虽符合民诉法关于执行财产为一般物的处置程序,但事实上侵犯了银行业监管部门的股东资格审查权,司法权取代了行政许可权,实为违法。
《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有对商业银行审慎监管义务,包括对商业银行股东资格及变更审查、批准,并授权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具体审查条件,即商业银行股东的变更需经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前置实体审查,故该前置审批属于典型的行政许可,归于行政权,非司法权范畴。具体到上述情形,银行业监管机构尚未对购买者或申请执行人是否具备商业银行股东资格进行审慎性审查,更未批准,即二者在尚不具备取得商业银行股东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即裁定其享有股份,继而成为股东,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于“以裁代行”,更使得二者后续能否实际成为商业银行股东存疑。需特别注意的是,前述前置审批不同于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后者为行政确认,法院可直接要求协助变更。
(三)执行中能否追加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为被执行人
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执行和解的,为保证被执行人及时兑现承诺,时常有被执行人提供担保人,且担保人在法院的执行和解笔录中签字。如被执行人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申请执行人能否申请法院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要厘清此问题,需对执行中的担保类型作出梳理。
执行中的担保分为两类,一类是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一类是执行担保。二者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同,前者适用民诉法第230条,后者由民诉法231条予以规制。接受担保的对象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执行中不同的处置方式。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系担保人向申请执行人作出,执行担保系担保人向执行法院作出。根据民诉法第230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法院依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里特别需注意的是,恢复的对象是“原生效法律文书”,而非执行和解协议,即执行和解协议即使由法院通过制作笔录加以确认,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相应附着的担保当然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此种情形法院不得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若想追究担保人责任,只能另行诉讼解决。与之相反的是,民诉法第231条赋予了执行担保强制执行力,法院可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故实务中,应特别注意上述两种执行中担保的区别,二者看似相同,实则法律效果千差万别。
四、本文结论
本文基于对执行异议相关规定的梳理,得出其实质性区分标准,并针对执行异议中若干争议情形作出简要论述。鉴于目前缺乏对前述问题予以有效规制的具体规范,实务中,应从执行基本原则出发,兼顾执行效率,准确区分执行异议种类,注重执行财产处置程序,并审慎追加被执行人。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司法执行实务的难题,但这一难题在近些年得到了有效改观。一方面,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大修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的有关执行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达34件。通过这些文件的出台,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有关执行措施、执行分配制度、执行救济程序等内容,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最高院在2016年全国“两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而后法院执行工作一直处于“高压”状态,2018年更是被称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年。基于此,“执行难”得到基本解决是可期的。但与之相比,有关执行救济程序的规范仍有待完善,特别是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标的异议如何区分以及实务中仍大量存在的“已裁代审”“以裁代行”等情形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造成实务中认知、裁判的混乱。笔者认为,针对此类问题有必要加以厘清。
二、执行异议的分类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225、第227条依据执行异议对象的不同,将执行异议分为执行行为异议、执行标的异议,并针对两种异议设计了不同的处置方式、法律效果。但前述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据此最高院制定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为执行异议的实务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可即便如此,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亦未对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标的异议的区分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异议人、执行法院在提出执行异议、审查异议案件时的法条援引出现混乱,特别是当事人以外的人提出异议时,如何判断其究竟是执行行为异议中的利害关系人,还是执行标的异议的案外人成为难点。笔者认为,前述两种异议的有效甄别,应当采取形式判断与实体判断相结合的方法,即首先根据异议主体加以判断,再行考察异议所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具体判断路径为:(一)异议主体。
根据民诉法第225、第227条规定,执行行为异议的主体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执行标的异议的主体为案外人。其中,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均为执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故执行异议主体为当事人的,则其只能依据民诉法第225条提起执行执行异议,此时仅做形式判断即可,无须实质分析异议对象究竟是执行行为或执行标的。当然,此种判断亦仅限于异议主体为当事人的情形,若异议主体为当事人以外的人的,则须按照第二项标准加以区分。
(二)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
从上述两种异议制度创设的目的来看,执行行为异议的目的在于纠正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以维护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程序上的利益;而执行标的异议的目的在于排除对特定标的执行,以保护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利。故二者的区分,特别是“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的区分,应紧扣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如果异议对象是执行标的物,且依据的是对该标的物享有的所有权等足以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则构成执行标的异议。反之,如果异议对象仅限于执行行为,或异议对象为执行标的物,异议人对该标的物亦享有实体权利,但该实体权利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比如排除超标的查封、法院违法拍卖侵害异议人对标的物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的,则为执行行为异议。即执行标的异议实体上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异议人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二是该权利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需注意的是,这里的的权利不仅仅局限于所有权,还包括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可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规定,异议人系待执行不动产的买受人,其在该不动产被查封前已签订有效书面合同且合法占有、支付价款的,可依据享有的债权申请排除强制执行该不动产。
简言之,执行行为异议与执行标的异议应按照异议主体之形式判断与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之实体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加以区分。前述两种异议中的“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虽同属执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但其异议依据的基础权利性质大不相同。因此,只有充分理解两种异议的实质性内涵,方能在实务中准确援引、适用相对应的法律条文。
三、执行异议若干争议情形
随着近些年执行措施的增多、执行力度的加大,相应执行异议案件的数量亦随之增加,其中一些异议情形因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成为实务难点。笔者以在实务中常见的且具有较大争议的三种异议情形为例,以探讨相应执行行为之合法性。
(一)执行中能否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
实务中,不少法院在被执行人无财产或无足够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裁定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笔者认为,该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且有违民诉法基本原理,属“以执代审”,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
1、违反民诉法基本原理
执行仅为实现生效判决内容,其不能突破或改变生效判决确认的责任承担主体等实体内容,涉及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及责任承担主体等实体问题只能在审判阶段解决。在执行中以裁定方式确认执行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被执行人配偶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等实体内容,并继而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追加异议人为被执行人,显属“以执代审”,明显突破了生效判决对案涉债务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
2、无法律依据
最高院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的变更、追加专门制定了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详细列举了民事执行中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且无兜底条款。其列举的情形中并不包括追加判决确认的债务人配偶为被执行人。另从该解释的精神看,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仅限于原被执行人死亡、注销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而仅因被执行人缺乏清偿能力,就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亦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精神。
3、最高院早已严禁此类追加
最高院数次通过判例、新闻发布会等方式阐明“执行不能改变判决”“严禁以执代审”。特别是2016年3月3日,最高院杜万华法官答记者问时,明确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本身就是司法审判的裁判标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只能在审判阶段不能在执行阶段。”,并特别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认定。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
(二)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审批,能否裁定对商业银行股份“以物抵债”或拍卖后归购买者所有
实务中,不乏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为商业银行股份的情形。一些法院在对该股份处置时,通常先行拍卖,拍卖成功的,裁定该股份归购买者所有;两次流拍的,裁定“以物抵债”,即该股份归申请执行人所有。上述做法虽符合民诉法关于执行财产为一般物的处置程序,但事实上侵犯了银行业监管部门的股东资格审查权,司法权取代了行政许可权,实为违法。
《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有对商业银行审慎监管义务,包括对商业银行股东资格及变更审查、批准,并授权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具体审查条件,即商业银行股东的变更需经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前置实体审查,故该前置审批属于典型的行政许可,归于行政权,非司法权范畴。具体到上述情形,银行业监管机构尚未对购买者或申请执行人是否具备商业银行股东资格进行审慎性审查,更未批准,即二者在尚不具备取得商业银行股东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即裁定其享有股份,继而成为股东,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于“以裁代行”,更使得二者后续能否实际成为商业银行股东存疑。需特别注意的是,前述前置审批不同于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后者为行政确认,法院可直接要求协助变更。
(三)执行中能否追加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为被执行人
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执行和解的,为保证被执行人及时兑现承诺,时常有被执行人提供担保人,且担保人在法院的执行和解笔录中签字。如被执行人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申请执行人能否申请法院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要厘清此问题,需对执行中的担保类型作出梳理。
执行中的担保分为两类,一类是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一类是执行担保。二者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同,前者适用民诉法第230条,后者由民诉法231条予以规制。接受担保的对象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执行中不同的处置方式。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系担保人向申请执行人作出,执行担保系担保人向执行法院作出。根据民诉法第230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法院依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里特别需注意的是,恢复的对象是“原生效法律文书”,而非执行和解协议,即执行和解协议即使由法院通过制作笔录加以确认,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相应附着的担保当然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此种情形法院不得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若想追究担保人责任,只能另行诉讼解决。与之相反的是,民诉法第231条赋予了执行担保强制执行力,法院可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故实务中,应特别注意上述两种执行中担保的区别,二者看似相同,实则法律效果千差万别。
四、本文结论
本文基于对执行异议相关规定的梳理,得出其实质性区分标准,并针对执行异议中若干争议情形作出简要论述。鉴于目前缺乏对前述问题予以有效规制的具体规范,实务中,应从执行基本原则出发,兼顾执行效率,准确区分执行异议种类,注重执行财产处置程序,并审慎追加被执行人。
主要联系人

高全
律师